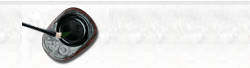|
|
|
忆陶老二三事
—纪念恩师陶博吾先生诞辰110周年
万长来
今年是恩师陶博吾先生谢世十五年,又是诞辰110周年。回忆往事,先生音容笑貌犹在眼前,先生的恩泽厚惠淡而弥永,我对先生的怀念之情,更是有增无减。
先生晚年,我曾在先生身边学艺近二十年,对先师治学态度严谨,生活自律简朴,以及在诗书画等方面的艺术造诣和做人风骨无不耳闻目睹,受益良多。
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头一春,我即拜师陶博吾先生门下,并有幸被其收为入室弟子。其时,老先生刚刚从下放的新建农村回城不久。我因自幼酷爱书法美术,报名参加了区文化馆的书法艺术班学习。陶老是这个班上最年长的一位书法老师,我则因此与先生结缘相识。
先生以近八十高龄之身,对我这个态度恭敬的小晚辈,从不以为距离。从那以后,陶老以其自成一家的艺术风格和朴实为人的大家风范,深深地熏陶着我、感染着我。从那年开始,我就再也没离开过先生了。
那个时候,授业老师有好几位,不知何故,自己却唯独喜欢上了陶老先生的艺术。若要论陶老书画如何如何的好,彼时的自己还真说不出个所以然。只是一种心灵的相通,觉得自己喜欢陶老作品所表达出的意境,总觉得陶老作品中表达出的东西,与自己心里的所思所想是一致的。先生的书画,仿佛就是自己所要追求的一种境界。
陶老见我学艺心诚至极,不但收我为徒,而且呵护有加。学艺之初,我从临摹开始,笔耕不辍,相信勤能补拙。自己每次把习作送给先生批改,先生总是很兴奋于我的点滴进步,对不足之处,则耐心指出。
1983年秋天的一个下午,秋高气爽,先生约我在老房木屋二楼的厅堂里坐下,自己在一把躺椅上半躺半坐,说:“长来呀,你跟我学艺多年,进步是有,这么多年我觉得你人老实本份、能吃苦、有钻劲、尊师爱幼,非常厚道。但在你身上还缺少了一种东西,那就是知识。你现在所读的书太少,底子太薄。要想取得非凡成绩,就一定要博览群书,多读些好的书籍,如唐诗宋词元曲等等。古语云:腹有诗书气自华。只有多读书,读好书,才能把先贤的东西化作我用,才能把书卷气、山林气跃于纸上及刀下也。否则,到头来还是写不好字,画不好画的。你现在读书太少,还没有读到我读的书的百分之一。”接着,老先生起身到书房里拿出一本《芥子园画谱》说:“这个画谱是解放前的版本,图文并茂,尚精又细,无论是学习看读临摹都是很好的范本,要多看看这类的好书。”同时,还列摆出了一大批要读的好书名字。
人生良师难得。为表心迹,我专门设下酒宴,请来同仁益友,当场为先生俯首敬茶,行正式拜师礼。自此,我将陶老视为再生父母,每到年节,我都要行师徒孝道,登门看望老师。
先生幼年饱经国家患难,深知一米一布得来之不易。其对生活起居从无过高要求,每日粗茶淡饭,简朴至极,故以“简朴”为家训,曰自己的书斋为“简朴斋”和“三破斋”。先生晚年有个习惯,就是常常将作画习字用过的废旧字画稿撕成小片,再细心收存下来,留作擦拭鼻涕之用。他说,别人嫌它脏,我却羡它香,既省钱又管用,方便好使。先生又说道,这些纸张的原料都是取之于天然,经工人手工所造,饱含他们辛苦劳动的汗水。虽经涂鸦已无用处,但并不脏,还有墨香味,我把它拿来作手帕之用,正是物尽其用呀。
陶老晚年,身体很是健康,五脏六腑都没有毛病。然而,毕究是八九十岁高龄的老人。俗话说,人吃五谷杂粮,难免会有伤风感冒。每遇感冒咳嗽时,先生行动总有些不便,其日常生活起居多由家人在旁搀扶、照应。我印象中最深的事,是晚年的先生爱让我为他洗头理髪或修剪指甲等。
陶先生刚返城时,头髪总是由一位民间挑担子的理髪师上门打理,到了80年代末期,这位理髪的老先生不见了。先生与我谈起这事,有些為難。……我听后便说,这个事簡單,我能做到,并自信地说自己理髪技术还不错,理髪工具家中都有,很早以前我就会此道。起初,先生半信半疑,经过几次实践,先生完全接受并肯定了我的技术和认真细心的态度。从此,先生的头髪洗理就由我负责上门包办。
每次理髪,先生总是提前带口信或直接打电话,约好时间叫我上门,一般先生都会选一个很好的时日,要么天气凉爽,要么风和日丽。如果是酷夏,先生就会安排清早或傍晚,以避开高温时间。如果是先生打电话,他一定非常謙和客气的说“麻烦你来我处一趟,帮我理个髪。”这句平实的话语一直非常清晰地銘刻在我腦海的記憶里。
在理髪的过程中,我会根据老先生皮肤皱褶多的特点,细心认真,缓慢推剪。洗头时,根据当时室外温度来定水温,保持水温不冷。有一次冬天我用温吞水給先生洗頭,他就说不舒服,從此以後,在冬天給先生理髮洗頭時,就會把水溫略調高一些給先生洗頭。
先生头皮十分的多且非常柔软,有一层层白白細細的油腻,我一边轻轻不停的抓挠,先生就一边不停的说“舒服,好舒服,我就喜欢你剪你洗,水冷了还帮我换盆热水再洗。……”剪洗好后,先生总爱说“理一次髪比吃一顿肉都舒服……”
先生一生命运多舛,却视艺术为生命,不弃不舍,且著作颇丰,不仅吟诗作画,且有不少珍稀藏画。如我所知,就有明末大名家宋旭,清代名家王石谷,近代王一亭、潘天寿、贺天健、王个簃、诸乐三、诸闻韵等名人名作。 这些名家之作大都是先生倾其毕生心血,精心所藏。
先生对其所藏的名家作品从不视为私物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先生得知杭州筹建其恩师潘天寿纪念馆,正在四处收集潘天寿先生书画作品,杭州筹建馆的同志知道陶先生是潘天寿的学生,便来信向陶先生征集。先生没有犹豫把自己一幅珍藏了五十余年的画作寄给该馆,以供大家纪念。可是后来开馆,我去了潘天寿纪念馆,问及陶老师寄来潘天寿先生画作之事,不知为何,纪念馆却告知没有收到此画。对此,先生却十分坦然,毫无悔意,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“好事没做好呀。”
1989年,先生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陶博吾诗书画展览,虽然遇上“89学潮”,但无论是从参观的人数,还是层面等诸多方面来看,举办都是非常成功的,可谓轰动京华,反响强列。当时我陪同先生参与了展览的全过程,中国画泰斗李可染先生,中国书协主席启功先生等都到场祝贺观看,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肯定。周谷城副委员长还把陶先生接到自己家中,两位耋耄老人一见如故,畅叙诗画艺术,谈笑风生,气氛十分和谐融洽。
其间,先生在北京就对我说起“不能让老实人吃亏” ……。展览结束后,一回南昌,先生就给我画了一幅四尺对开的菊石图,专门题了诗和上款。同时还给我的夫人画了一幅,画好写好后,并写信来叫我去取。我到了先生家,先生很高兴对我说,“长来呀,你平时很少开口讨要我的字画,我一直放在心里,这次来北京你出了很大的力,辛苦了,我记着你呢。”接着,又说:“你就像我们陶家的人,但不姓陶,将来分不到陶家的财产,可我永远可以给你写,给你画。”……闻听此言,我全身犹如暖流穿过,感激不已。
1993年,当时的南昌铁路局电视台成立不久,决定拍我一个专题片,这也是电视台成立后的第一个人物专题片,片名为《笔墨春秋》,是由原江西省军区副政委、江西省书法家协会首任主席王一琴先生题写。根据编导安排,片子里要拍一节我跟先生学习艺事的镜头。事先虽已和老师打过招呼,但具体时间一直未定下来,只告诉先生可能会是晚上。
彼时,恰是寒冬季节,先生已是九十有四高龄。当我们赶到先生家里时已近晚上十点。先生早已上床休息。我一进门,就直奔先生床前和他打招呼。先生说,这么晚还拍电视,我从来都没有过,一边说着,一边在我的帮助下,坐起身来,穿衣下床,在书房兼卧室的书桌前坐下。经过简短的介绍,老师很是配合地摊开画案为我作诗题字,十分愉快地补上了这样一段镜头。同时,高兴地把 1993年第四期封面封底及首页等介绍自己专题的《中国书法》杂志,用毛笔签上自己的名字送给了当时前来拍片的杜台长。一切妥当后,我更加深感先生对学生的成全爱携。
在先生的教育下,我从不热衷声色娱乐场所,生活也很是简朴,喜欢自然、游历山川。三十年来,我平时最喜欢的事就是看书、写字、作画、治印,这几乎成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事情,日月往返,从无间断。
先生驾鹤西去头一年的某日,我把自己写好的字画和一本印稿交老师批改,先生对我字画的进步给予极大的肯定,同时提出了宝贵意见,寄予了厚望。
老师看到我刻的印章有一百多枚,便主动地说:“长来,看得出来,这些年来,你在这方面是用了功力的,这印刻得不错,可以出一本小集子,我愿意为这本小集子写点东西。”并与我约好第二天下午3时半上门。
此事定下后,我一时兴奋异常,开心不已。谁知第二天,一位亲戚相邀吃午饭,我在席上却因一时高兴喝高了。离开酒桌本想按约定去老师家,谁知走不多远,便醉倒在地。一觉醒来天色已晚,四周灯火阑珊。立时我自语道,不好,误事了。随即就来到一个公用电话亭给先生家里去电话,老老实实地把情况告诉了老师。我对老师说,自己因为喝酒不能自控而误了大事,弟子我教而不化,真是深感无脸见人,我再也不去你家学习书画了。
先生接到电话,一边劝慰,一边告诉我,喝酒本不是坏事,但要少喝,不要喝醉就好了。老师一番安慰,让我心宽了许多,但还是自觉对不住先生,执意不登先生家门。先生反复劝慰无果,竟又让其孙南强来我家劝说,称年轻人知错即改,不必深责,如果仅以此小错而断送师生情谊,岂不更误学业。
先生如此厚德和宽容,让我的泪水感动如雨。先师的诚心关爱,更让我今生永世难忘,无不敬佩极至。我决定不再一味纠缠于此事,一定要振作精神,加倍努力,决心要以更坚诚的学艺来回报先生。此后,我更加珍惜时间,学习努力更加省悟。事到如今,我每当参加酒席,均牢记先生之教诲,再没有过贪杯误事之事。
先生晚年声名在外,向其索要字画的人众多,先生不分贫富贵贱,总是有求必应。有一次,我去先生家里看望先生,先生主动将其已画好的一幅花鸟画送给我,而我却没有收下来。先生问道,为何不要?难道是画得不好吗?我说:“这幅画我很喜欢,可是我不敢贪婪,我想要一幅有很多古松的山水画。”先生说:“那好,我来帮你画。”后来这幅画画了许多松树,山势等等,构图基本画就,只是没有来得及设色和题字,直至先生驾鹤仙逝,这幅未画完的画就成为了历史绝唱。
后来,这张画移交给了先生的儿子陶澄,谁知先生的儿子也一直没有动笔补就。2002年6月,陶澄先生又离我们而去,这张未完的画最终又由陶老的家人交给了我。现在,这张画我依然保存在档,我更视为永久珍藏。
仿佛转眼间,先生离我而去已经十五年了,我与陶老一家人的相处仍是和睦愉快,我非常珍惜这种融洽之情,并将此情延续至今。
老师虽然离我而去,但他的人格、他的艺德一直在影响着我,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。
庚寅秋于邀月楼南牖 |
|
 上一篇: 陶博吾先生题一 上一篇: 陶博吾先生题一 | 2009/5/11 11:26:10 [6460] |
 下一篇: 没有了 下一篇: 没有了 |
|
| |
|
|